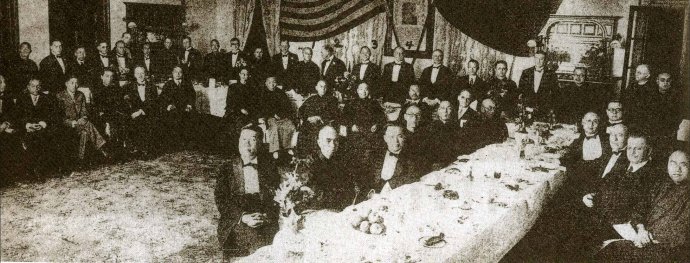转型时代:企业家阶层的选择
傅国涌
我们从更宽阔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待企业家阶层的选择,放在一百多年中国企业史这个框架里面来看企业家阶层要面对的社会转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看历史常常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或者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我想说,历史研究本身就是要将复杂的问题复杂化。我对此有非常深切的体会,如果不能把复杂的问题复杂化,最终得出的那些结论可能都是错误的。所以我更看重历史的过程,而不是看重历史的结果,就像生命也是一个过程,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宗教感的国家,历史具有准宗教的功能,中国这一轮的改革,也是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开始的。 历史不仅是关乎过去的事,更是关乎未来的事,历史直接通往未来。
现在这个时间是2013年1月21日下午13点43分。这个时间点,其实不是“中国时间”,而是“世界时间”。我们今天既然认同从秒、分、小时来计算时间,这个时间就不是中国数千年来固有的,我们可以它称为“世界时间”。从“中国时间”进入到了“世界时间”,这是近代以来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连我们的计时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过去的计时方式更多的是按季节、按照播种、收成、农业社会的节奏来计时的,从“中国时间”进入“世界时间”意味着中国的文明状态,也是从农业文明状态开始往工业文明状态转换,这个转换跟中国近代以来的企业史大致上是同步的。
过去我们之所以讲,中国的文明模式是农业文明,我们今天讲中国已经进入工业文明(或工商业文明),甚至信息文明的时代,表面上看,最大的变化就是生产方式的变化,这个生产方式是农业还是工业。生产方式的变化必然要带来整个社会与之相匹配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它的公共生活方式和他的精神生活方式都要发生改变。今天中国很多的困境、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痛苦就是因为生产方式变了,但是体现在生活方式上只有物质生活方式发生了某些相应的变化,它的精神生活方式和公共生活方式还是没有变,骨子里还是过去古老的方式。我把生产方式的改变称之为文明的表面,文明之表,包括我们的物质生活方式都可以称为文明的表面,今天文明的表面已经换过来了,文明的里子还没有换,里子就是我刚才说的公共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整个西方社会的变化也是这样,当它的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之后,机器工业和近代工商业兴起以后,它整个的精神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包括哲学观念、娱乐消费的方式等等,整个都随之发生变化,议会民主制度,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并不断成熟起来的。这是公共生活层面相应的一种转换。
中国文明之表与文明之里的变化不同步原因很复杂。中国的转型不是一个自生文明自发转型的结果,它是外在的外力强迫型的被动应变的一个结果,不是自发生长出来的一个秩序。我记得哈耶克先生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在演讲里说的,文明不是人的大脑设计出来的,而是从千百万个人的自由努力中生长起来的。我特别喜欢“生长”这个词,讲中国近代史可以讲一百年乃至150年,或者可以讲205年,这是马礼逊传教士到中国来的那个年份,看做当作近代中国的开端。200多年来的中国,是外面压迫你应变,不是你自己内部自觉地、主动地求变。如果按照原有农业文明的生产方式,由它自身演变下来,会变出一个什么结果来,今天已经无法反推了。我们看到的是外部因素,基督的福音,坚船利炮,不平等条约,西方工业品进入中国市场,报刊,新式教育,法律体系……,导致我们被动应变。这种被动应变到今天的一切都是不同步,表里不同步,就是文明之表和文明之里不同步。我们中间的转型出现过多次的断裂,其中有彻底的断裂,这种彻底的断裂带来的后果今天看到了。我说转型有两种,一种是延续性的转型,一种是断裂性的转型,从晚清到民国的转型是延续性的转型,整个社会结构没有变动。所以鲁迅的小说很不同意辛亥革命,整个社会还是那样的一个状况,其实辛亥革命的局限也就是辛亥革命是它的优势,他的失就是他的得,有时候我们在得失之间往往只看一头,得失其实是相辅相成的,相互成全的,得不一定都是得,失也不一定都是失,失和得之间也是一个相互成全的关系。
辛亥革命是有限革命,就是限定在政体革命的范畴以内,就是政治体制的范畴,不涉及整个社会,不把整个社会翻个底朝天,不进行财富的重新分配。这是很关键的,不进行财富的重新分配也就是说过去的富人还是富人,过去的精英还是精英,士绅阶层和富人阶层不会因为政体改变就变得一无所有。
刚才冯仑先生特别讲到张謇,我对“张謇模式”是持非常肯定的态度。从时间跨度来说,“张謇模式” 是横跨晚清和民国的,张謇从1895年开始办工厂,1900年工厂开始冒烟,如果从1900年算起,他的黄金时代是22年,他最后的鼎盛时期是1922年,这也是中国企业家的黄金时代,1922是中国企业史的巅峰状态。他是1926年死的,这20多年,张謇模式横跨了清晚和北洋时代。民国早年的这个北洋时代,“张謇模式”仍在积累当中,企业家这一群体有特定的内涵,是做生意的。汉语中“生意”这个词很有意思,你看看前面是一个“生”字,生生不息,天地之大德就是生,生也有生命的意思,有生长的意思,有活的意思;后面是个意字,有那么点意思,而且他这个意思是一个大意思,不是小意思,它关乎天地之大德的意思,所以中国人把“生意”这个词,起得特别有内涵。生意是需要积累的,不是说你做个一两年暴发户,暴富了,这就叫生意,生意是要传承的,生意是要积累的,生意是特别强调要给它时间,要有一个稳定和平的相对较长的外部环境,他才能够把生意逐渐地从小做大。中国的生意往往都是从零开始,从无到有、无中生有,然后从小到大, 中国企业家这个角色在本质上是一种建设力(当然不是唯一的建设力)。可与中国的农民起义相对应,农民起义作为历朝历代洗牌的一个主要方式,另一个方式就是宫廷政变,宫廷政变跟农民起义其实是一致的,都是以暴力为基础,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破坏力。中国社会的洗牌,包括维持中国的社会格局,基本上是靠破坏力,有时候你看到破坏力是摧毁次序,其实破坏力不是摧毁秩序,破坏力是更新秩序。农民造反的领袖不是为了毁灭旧王朝的那一套制度秩序,它是为了维护旧王朝的那一套秩序,他要更新那一个秩序,只换人不换制,这是中国特色。这个破坏力是中国生生不息的一种力量,但是中国的建设力自古以来是非常薄弱的,如果把企业家阶层的起点放在张謇那一代,他们是洋务运动、甲午战争之后产生出来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作为中国企业史上最早的那一拨人,他们代表的是一种建设力,这种建设力是新生的力量,他在农业文明社会当中不可能产生的,只有在出现工业文明转型的这个时候才产生出来,这种建设力,就当时的时代来说,它是以一种相对独立的状态出现的,它更注重的是社会层面的建设,我称之为底部建设。通过他们的机器生产,通过他们介入这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来重塑一个新的社会,张謇在南通提出的理想,他用了一个词叫“村落主义”。
他说我改变不了中国,就改变我的家乡南通吧,中国太大了,无从下手,南通我够得着。所以叫村落主义,他把自己的理想,他给自己设定的路径方向,用八个字概括,“得寸则寸、得尺则尺”。
他不想得寸进尺,也不想得尺进丈,不想天上夜给他下馅饼儿,他不着急,慢慢来,在南通做大量的建设。他觉得,把南通搞好了,他一生的本分就尽了,所以他创造的这个模式我觉得最大的意义不在于张謇本人在南通做了那么一块,而在于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参照系,给后面很多其他地方的企业家和后世的企业家提供了参照。
这比张謇本身所做的意义要大得多,当年影响了无锡的荣氏兄弟,范旭东在天津也想学他,浙江温州平阳县的一个士绅,他叫黄理孚也想学张謇,中国要想学张謇的人,“小张謇”在中国当时许多县都出现了,所以它的辐射意义,要远大于它本身在南通的意义,袁世凯是看到这一点的。袁世凯称帝之前,1915年他曾经叫熊希龄跟张謇说,把南通建设的成绩汇编成一本小册子,然后印发给全国各县来学习,这本书后来编好了,因为袁世凯做皇帝了,这本书就没有发下去,这本书现在南通那边少量印刷,没有公开出版,主要列举张謇在南通推动的那些社会事业,就是他在企业之外所做的,甚至包括气象台都办起来了,什么养老院聋哑学校这些都有,覆盖整个社会方方面面,图书馆、体育场、博物苑、公园,南通有5个公园,凡是人有需要的,从精神的需要、物质生活的需要,方方面面他都有顾及。从企业史的角度来看,一开始张謇提供的就是这样一个标本,起点之高,令后人唯有感叹。
从100多年社会历史变迁的进程来看,中国的企业家阶层至少有过四次重大的选择。几乎每一代企业家都会遭遇自己时代的问题,并面临不可回避的选择。
中国企业家阶层第一次面对的选择是在辛亥革命前夕, 君宪还是共和?这是一个制度选择。我觉得这次选择事关重大,中国一百年来,没有一次机会让中国的人民有机会去做制度选择,无论最后选择的结果是不是如人意,后来变化如何,但在当时来看,清朝末年,中国人有机会做这样的一种选择,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当时中国企业家阶层,从他们主动的意愿出发,从他们的角色地位出发,他们大致选择了君主立宪,就是从整个阶层的多数来说,他们是选君主立宪,他们参与发起了至少三次国会请愿运动,规模都非常大,而且已经让清政府作出了部分让步,从九年立宪已经改成了六年预备立宪,已经答应在1913年召开正式国会,变成一个英国模式。但是1913年中国人已经等不急了,1911年就爆发了革命,其实时间上也就相差了1年多一点,但是有的时候一年也等不及,只争朝夕了。
这次选择企业家还是有相当的主动性,当时上海的预备立宪公会领袖就是张謇和汤寿潜这些人,汤寿潜是浙江人,就是领导修了第一条上海跟杭州之间的沪杭铁路,因为修这条铁路一分钱工资也没拿,一分钱的贪污都没有,所以他当年有极高的声望。当时上海的商界的代表像沈缦云、李平书、王一亭,后来都参加了辛亥革命的上海独立,其中沈缦云是上海商界的代表,他在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时,到了北京城,而且见到了一个军机大臣,他们之间的对话,登在报纸上面,就是谈论为什么不马上开国会,开国会就可以解决中国的目前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他们给出的理由无非中国国民程度不够,所谓国民的素质不够,跟今天的说法是一致的。第二次对话也是这个时候,跟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有一个对话,内容接近,也登在当时的报纸上,谈完以后,他对记者说了一番感慨,说,锅里水将要烧开了,里面的鱼还不知道,我以后再也不来了,就是表示跟清政府,跟朝廷没关系了,后来沈缦云就转向了革命,资助于右任创办了《民立报》。这一轮的选择,其实企业家阶层原本是选择君主立宪,但是结果发生了辛亥革命,当革命发生之后,他们大部分人都选择了顺势而为,不再坚持原来的君主立宪立场,而是赞同了共和立宪,赞同了民国,包括张謇,包括汤寿潜,他们两个都做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内阁总长,包括沈缦云沈这些人,都在上海政府担任了重要职位。
他们原本在制度选择上是主动的,最后当形势发生剧变之后,他们在被动当中仍然保持了相对的主动性,保持了尊严,因为最后他还是可以选择跟清政府站在一起,或者做出另外的选择,但是他们顺势而为,这个顺势而为,我觉得对整个民国的转型起了特别大的作用,保持了整个社会转型的稳定性,因为这批人,他跟今天的企业家阶层有一不一样的地方,这批人不光是代表了资本,他们不光是当时新兴企业的代表,他们更是中国士绅阶层的代表,他们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当时革命的结果。革命不是以最惨烈的结果告终,而是以相对较为温和有节制的方式告终,辛亥革命成为有节制的革命,流血较少、死人较少,最后是以几方妥协告终,包括隆裕太后也妥协了,他们是退位下来了,不是被枪打走的。尽管是在武力的压力下面,在整个社会的压力下面,由此我理解就是晚清跟民国前15年之间,有一种延续性,中间没有断裂,他们做出的选择是相对温和有节制的,这一轮的选择,我称之为良性互动,从1900年,或者1895年到1927年的中国基本上保持了延续性,中间不是断开的。
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中国企业史上的黄金时代从1915年到1922年,就是一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以后,到1922年由于西方资本重新回到中国市场,中国企业开始被削弱,1915年到1922这个中间不足10年的时间,是他们最好的时间,整个北洋时期中国的社会其实是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军阀之间的混战它是有节制的混战,不是以消灭对方为目标,而是以打败对方为目标。北洋时期的斗争不是那么惨烈的斗争,他给社会留出的空间还是相对较大的,所以我们才可以理解有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也是以和平的方式落幕的,如果不是因为他们都是比较有节制的,比较温和的,那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企业的黄金时代也只可能在这个时代。
接下来企业家阶层的第二次选择发生在1927年前后,这次选择我称之为悔还是不后悔?这次选择就是没有制度选择的空间,就是选择认不认可国民党,支不支持国民党,国民党黄埔建军,北伐是用武力打到长三角的,上海的企业家阶层,那个时候中国差不多40%的企业集中在上海,他们选择什么态度就决定整个阶层大体上是什么态度,他们支持了国民党,大概几个月以后就后悔了,他们发现这一个国民政府跟他们之间其实是根本合不来的,相互之间有很多的矛盾和摩擦,包括荣氏家族马上就遇到麻烦,蒋介石发通缉令要抓荣家的老大。
所以南京国民政府的这十年,1927到1937年之后称为“黄金十年”,这个“黄金十年”其实是从那个角度说的,是指国民政府统治大陆时代的黄金十年,搞了不少建设,后面就是抗日战争了。民营企业虽然还有一些空间,但在这十年当中其实是每况愈下,只有荣家还在发展,在荣家是负债扩张。整个中国企业在这个十年当中,新开创的企业很少,大部分企业都是在前面的黄金时代里开创的。黄金时代创办的企业、银行在整个中国企业中占有最大的份额。这个阶段我用一个词称之为中性互动,企业跟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中性互动的关系,已经没有良性互动了,1927年之后历史出现了部分的断裂,不是完全的断裂,有很多的摩擦很多的矛盾。当然随着1937年的到来,这个过程就结束了,比较短。
第三次选择是迁还是不迁的选择,1937年。第一次是君宪还是共和,还有制度选择,第二次就是悔还是不悔,第三次选择是你迁还是不迁,要么留在上海,留在东南沿海,留在天津,要么就迁到四川去,这次选择是因为民族危机引发的。不关乎制度,也不关乎跟政府之间的关系,而是因为外敌入侵造成的。
第四次选择就是1949年的选择,这次选择直接决定了我们今天,这次选择是去还是留? 是离开大陆还是留下来的选择。20世纪大变动的中国,一次一次的选择,走的是一条下划线,一百年前的选择还有机会选制度,后面的选择是后悔还是不后悔、迁还是不迁、去还是留?1949年这次选择的结果,就是没有互动,这次选择做出来之后将来再也没有互动了,1949年以后企业家阶层跟政府之间没有互动,没有任何的主动性,完全是被动,完全被动就没什么互动可言了,反正你是完全被动的。从此以后中国企业史出现了一个完全的断裂,这次转型是完全断裂的转型,1952年到1956年搞公私合营,要把整个企业家阶层连根拔起,当时统计的数据说,中国大概有400万的工商业从业者,包括雇工人数加上去是700多万人。当时的企业规模都不大,雇工人数在20人以上的只有8000家企业,雇工人数在100人以上只有三千家企业。比今天的企业规模小多了,不可同日而语。到1957年的年初,中国的所有企业都已经被灭掉了,中国没有一家民营企业,1957年的元旦一过,统计数据,没有一家可以称得上企业存在的,剩下的就是那些小店,一个人的开的那种小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今天如果说三十年来重新产生的企业家阶层又一次面临选择的话,也可以看出是第五次, 这次选择是一次同样非常艰难的选择,我不指望有良性互动, 如果能够回到中性互动,而不是恶性互动,或者是没有互动,那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次的转型的过程很可能是以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过的方式展开,我更看重这个过程展开当中,它呈现出来的那些事实,所以我说研究历史首先是做事实判断,而不是做价值判断。而历史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每个人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前些年提出一个看法,叫增量历史观,从增量历史的角度去看待,企业家阶层作为一种建设力,它应该是提供增量的。从它的本性来是,它是提供生产的东西,提供正能量的,是一个增量,所以今天可能要面临的是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我称之为路径选择,走什么路?第二个选择是制度选择或者方向选择,说制度选择可能有一点大了,有一点宽了,用方向选择可能更确切一些,到哪里去?
走什么路?到哪里去?这是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问题,刚才冯仑先生主要从生意的角度,从切身利益的角度,从跟自己生意有关的角度,最后自然而然的会逼到思考中国的一些困境,思考中国大的问题。从路径选择来说,我觉得张謇那个时候提供的那条道路是积累的、渐进的,就是后来胡适之说的“得寸进寸”的路,不指望天下掉馅饼一夜改变一切的那种路径,得寸进寸的路。今天其实我们也应该是一个更看重过程,这个时代可能不会马上有一个结果给你看到,从这个方向选择来说,今天大致上都是比较清楚的,其实张謇给自己一生一个定位,一生最大的成败就在立宪这件事上,他认为中国立宪没搞成,是他最大的遗憾。他指的是君主立宪,中国今天的方向其实也是立宪的问题,中国一直没解决立宪的问题,没有解决一百年前慈禧太后的问题,所以始终彷徨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国的生产方式跟它的公共生活方式不匹配的一种状态。
我觉得中国一百年来,我们看到的这条路,国人始终容易着急,所以每一次的思潮都是越来越激进,辛亥的时候他们只要求建立共和,到了北伐他们要求建立的是国民党一党政府,到了共产革命、国共内战要求建立的是一个一边倒的政府,要把整个社会摧毁,民间社会真正被摧毁是50年代,50年代是把整个中国过去几千年延存的民间社会都连根拔掉,重新恢复民间社会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到今天还只是这样的一个水准,中国没有任何就是真正独立的民间社团。今天来看我们这一轮的转型,我们所需要的选择,从心态上来说,可能更需要有等候的心,有节制有忍耐的心,因为中国的事情一着急就容易往更激进的方向去。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心态可能比专制更可怕,因为它最终导向恶劣的专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当年谁知道把国民党灭掉,将来会迎来一个更专制的政权?中国多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都是奔着民主自由去的,最后收获的不是民主自由,而是比原来还要糟糕,从自由的多少变成自由有无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想不到的,最近出的一个书就是给儿童看的,给少年儿童看的“新童年启蒙书”,有一本书《我是中国人》,封面上有一句广告词,“在古老的土地上崭新的成长”,我觉得这个广告词太好了。这套书一共有四本,一本是关于规则意识的,一本是关于生命意识的,一本是关于国家意识的,一本是关于财富意识的,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的。
第五本是关于信仰的,没出来,其实也是我们成年中国人要面对的这四个意识,这个意识归根结底就是公民意识。我觉得,在这些意识上面才有可能建造一个公民社会,我们今天要给这个小孩子说这些话,如果这些意识都不具备,中国是不可能有宪政的,宪政是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上面的,刚才讲到台湾的红衫运动百万人上街,能够收放自如,关键是这些人,已经有了这样的公民意识,他是可收可放的。中国大陆可能离这个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如果对天安门广场的这个运动有一些深入的研究的话,就可以看到也是越激进的人最终掌握了广场的发言权,比如你绝食,那好,我绝水,我比你还要厉害,那么我就比你厉害,我就领导你,那来了一帮人说,你绝水,我自焚,我比你还厉害,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如果还原历史的真相,将复杂的问题复杂化,有很多值得花时间去细细言说的东西。我们说生命的成长需要时间,一个人不可能从一岁明天就变成80岁,一个健康的社会的长成,同样需要时间,不可能用一年时间、两年时间就把一个原本破碎的社会建成一个健康的社会,这也同样需要时间。所以我们观察中国的现实,需要跟中国的最尖锐的现实拉开一点距离的,你如果跟中国最尖锐的现实抱成一团,你就看不到中国的现实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你需要拉开一点点距离,看它是什么状况,这也需要时间,需要尺度。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现在需要做出一些调整,需要从个体的角度考虑需要做什么。我想到一个词,就是特别是掌握了一定资源的阶层群体、个人,更有责任去做一些事情,用过去邓小平的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怎么办?我给出一个说法,让一部分人先文明起来,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要让一部分人先文明起来。文明这个词,在这里有一个特定的内涵,就是我前面说的,过一种跟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物质生活方式相匹配的社会公共生活、精神生活,这样的时候已经到来了,因为我们的生产方式改变已经多年了,我们的物质生活方式也改变很多了,都已经使用微博的时代,使用手机短信的时代,使用微信的时代,我们的精神生活方式和社会公共生活方式,也要与之相匹配。文明这个词的特定内涵,因为文明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文明,它还是精神层面的文明,和公共社会生活层面的文明,只有一部分人先文明起来,才可能推动这个社会整体文明起来,社会最终是生长出来的,是长成的,不是设计出来的,没有人可以在一个密室里设计未来的文明是什么样子,但是所有的明天都是从昨天开始,当然也是从今天开始,包括社会上出现很多教会,很多商会,这些可能都是社会成长的生长点,如果没有在信仰层面,没有在价值层面做出改变,这个社会任何外在的改变,都可能只是表。因为我们曾经有机会来建设一个共和国,我们曾经有机会创立了总统宪法国会,但是最后都毁掉了,毁掉有它的道理。任何东西没有在这个地上站住脚,一定有它的原因,有它背后的逻辑,如果说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候,我说今天是一个拆毁的时候,需要拆毁很多旧的东西,但是今天也是一个建造的时候,需要建设很多新的东西,企业家阶层作为一个掌握资源的阶层,任何社会的变革都绕不开这一部分人,无论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无论他们对政策上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或者在身体上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移民或者不移民。因为这个阶层就是这三十几年,甚至说这100多年来中国生长出来的一个社会人群。这个群体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是地上长起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也是想关注这个阶层未来的走向。
【根据录音整理】